發布於 05月17日2025年
1.1K
【新共和場邊側記:燕入金華盪海波── 盧秀燕為何這樣提《國家七安》戰略?】
注目焦點
- 【藍晒圖|〈吳展良:「孫中山思想:內涵演變與歷史實踐〉搶先看。】11月12日2025年
- 【藍晒圖|〈張智瑋:「數位時代的巨浪,國民黨如何因應?」〉搶先看。】11月07日2025年
- 【藍晒圖|〈施威全:「民族統戰話語,國民黨如何接招?〉搶先看。】10月21日2025年
- 【藍晒圖:重構國民黨黨務改革&人才甄補搶先看。】10月07日2025年
- 【讀者投稿|胖橘約翰:綠媒為何不打鄭?國民黨的死亡預知紀事。】10月05日2025年
- 【藍晒圖|〈吳展良:「孫中山思想:內涵演變與歷史實踐〉搶先看。】
最多人瀏覽
關注我們
圖文藝廊
This error message is only visible to WordPress admins
訂閱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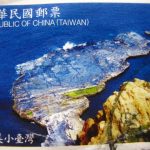













【新共和場邊側記:燕入金華盪海波──盧秀燕為何這樣提《國家七安》戰略?】
「媽媽市長」這個人設,算是台灣政壇近年來一個很成功也很自然的操作設定。不論是國民黨還是非國民黨的群眾、媒體,都普遍接受了盧秀燕這六年多來巧妙打造的這一形象標籤。
不過,「媽媽市長」以長女的形象進行更上一層樓的「政治歸寧」,倒是一道罕見的風景。
在520民進黨賴政府上任周年將屆、朝野各路勢力和鋒頭各自進行盤點總結的這一時間節點,盧秀燕以淡江戰略所「所友回娘家」的身分,回到臺北金華街的淡江大學城區部,在「淡江戰略學派」的年度研討會上,展現了自己把視界投射出地方治理之外,眺望更廣闊層次和更高位全局性議題的起手式。
「我是本科系的,我是正科班的」、「我是淡江戰略學派的一份子」。
盧秀燕在演講的開始,便用親切的口吻歷數淡江戰略所師長對自己的教誨和幫助。在長達十五分鐘的致詞中,這段細數自身與母校母所淵源的段落,就佔了大概近半。較為別緻的是,除了強調自己的師輩淵源橫跨藍綠、國安人才也不應有顏色陣營之分外,盧秀燕也陳明,自己雖然是從地方選區的國會議員出身,但自始便對國家安全、國際關係非常有興趣,長達13個會期都擔任立法院國防外交委員會的召委,最後更以《國家安全與國會機密預算》作為畢業論文的主題,並得到後來也受到扁、蔡政府重用的兩位學者──林正義的論文指導和林文程的論文審查。
在政治人物的論文品質備受社會檢驗的當代台灣,在二十多年前就畢業的盧秀燕不無自豪地說,「戰略學術沒有分藍綠,他們對我十分嚴苛」,「各位老師,各位學長,各位學弟妹,如果不是論文那麼嚴苛,我今天不會站在這裡」,「我選舉九次,一次省議員,六屆的國會議員,兩屆的市長,聽說我的競選對手把我的論文翻爛了,就是希望能夠找出我的毛病,可是到現在我還站在這裡」。
一段段力圖讓台北媒體「記起」自己曾有扎實國安外交知識歷練的憶舊,就在對母所的孺慕感懷與對師友情誼的勾勒中自然托出,把頗為政治的信息,自然嵌合在看上去並不那麼政治的家常話語裡,這是盧秀燕的立身技巧之一。
隨後,她才切入這場致詞的核心──盧秀燕的「國家七安」戰略觀。
這七項安全議題在講稿中自然排出了順序、但盧秀燕又說,實際上它們不分先後、同等重要的主題是:公衛安全、金融與經濟安全、能源安全、資訊安全,再來是涉及天災地變的國土安全、外交安全,最後才是最傳統和最硬的──軍事安全。
盧秀燕指出,戰略所大家當年在課堂上曾經推演過的戰略假想,在過去十年中,都一一發生。
有趣的是,雖然談的是國安和外交的主題,但仍維持一貫持盈保泰,不願輕易顯露自己國際關係站位的盧秀燕,卻多以COVID-19造成全世界Shutdown三年、網軍攻擊恐造成全國人民的財產不翼而飛等概念性、場景性的案例作為簡要闡述的例子,而甚少提及具體的國家和或國際關係中的行為者。
少數有實質觸及的,一是點名川普總統的關稅政策,讓全世界的國家領袖總動員,「因為如果沒有妥善處理,一個國家它的經濟金融可能會崩潰」。
二是用以巴衝突做例子,含蓄而隱諱地說:決定勝利與否的,不僅是軍事武器上是否能夠摧人,還要看一國的外交安全,能不能夠得到各國的支持。
三則是在回憶Covid19公衛教訓的段落,扼要卻別有意味地提到「這10年來發生的災情,會給很多的戰略學家去思考:今天的武器可能不是只有軍事武器;病毒的研發、疾病的產生也是一種武器」。
綜觀下來,可以看出,與其像綠營政治人物那樣使用在川普時代其實有點過時的「威權vs.民主」的新冷戰台詞腳本,盧秀燕則完全採取另一種切入視角,表達她的國安關懷點。
包括她不諱言川普的關稅政策,確實給全球各國帶來了嚴峻挑戰;但也不完全否定西方深層體制中所流行的敘事──即把疫情和病毒作為一種攻擊方式的武器化擔憂。
而用以巴問題做例子,則試圖展現她自身在人道主義議題上的關懷,呼應聯合國多數國家的投票選擇,對於只靠武器優勢、不顧全球外交輿論評議的單邊主義作法,表達了含蓄的不予苟同。
相對於綠營執政這九年來所習慣的逢美必從、逢美必誇必跟,盧秀燕毋寧展現了另一種台灣潛在領導者的多層次思考。
但是,但在涉及國際關係「大是大非」的關鍵議題上,作為國民黨人的盧秀燕,在近年來國際輿論中藍、綠陣營被傳媒標籤化地簡化二分為「反軍購」和「挺軍購」兩派的危局下,她也利用戰略所「戰友」的身分亮明立場,直接了當地說,「我個人是支持我們國家要增加國防預算的」!
她說到這裡便俐落打住,沒有再延續藍營一貫的說法,例如繼續解釋「國民黨嚴審國防預算是要確保研發方向和策略正確」、是要「在美國賣方面前主導國軍自身建軍方向」等,避免進入治絲益棼的細節探討。而作為一個地方首長,人們似乎對此也不太容易苛責。
而整場演講第一時間被大多數電子傳媒擷取的,則是她肢體動作最活泛、議題涵蓋也最有駕馭國政架式的一段話──「你不能想像國家安全的破口在哪裡,所以我提出的第一個建議是,我們應對國家安全的面向,擴大做全面的準備──不要排序,也不要選擇。換句話說,國家安全的工作,不是只有國安會、國安局、國防部的事情,金管會、財政部、衛福部,你統統要準備起來」,末了,還有點俏皮地再度誇讚自己的母所,「如果這些部長不太懂,可以來請教淡江戰略學派」。
緊接著,則是以「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的老話,加上引用身具淡江戰略所老師和國民黨國際部主任雙重身分的黃介正之言:「備戰才能夠迎戰,強軍才能夠維和」,「寧願備而不用,寧願一直不來,但是我們有所準備。平常的準備功夫是國家要跟人民溝通的,要讓大家一起全力以赴」。
而指點部會分工、動員國民心態,對戰事的可能降臨提出預警,並從破題就強調「雖然我現在在地方從事治理,但是我還是有長期的本能反應,關心國際情勢的變化、關心國家安全、關心戰略國防政策」,盧秀燕下一步要做什麼,雖然她自己不點透。但此刻,她願意公開傳遞的思緒,則已遠遠超乎一位地方城市首長的傳統考慮層級。
在520前夕的這個星期六,盧秀燕以傑出校友、所友的榮耀姿態回到淡江母所,疾呼這是一個「最需要戰略家」的年代,給足母所上下光采。而筆者們於現場觀察,台下淡江戰略所的師長們,也無不以「吾家秀女初長成」的欣慰眼光回視。「淡江戰略學派」群英(鷹)們的未來,似乎也會跟著燕子一同騰飛雄起?
而在一個縱論國安與外交的場合,最顯眼的留白、最引人矚目的未著墨處——當然就是中國大陸的角色,和台灣與其互動之道。
不論是九二共識、大陸、北京、對岸、中國,甚至市「兩岸關係」四個字,在盧秀燕這篇15分鐘的致詞中,通通沒有出現。對傳統的國民黨政治人物來說,這當然是一個罕見之舉。
這樣的慎重,顯然與盧不想過早地浮現自己的兩岸路線和論述,以免樹大招風、提前招來敵方火力有關。
一些論者──包括新共和主筆室自身也曾預示道,隨著國內國外格局的改變,下一階段的國民黨領軍人物在兩岸上的主張,恐怕不能只是簡單地對連、馬時期以降的路線和種種說法加以繼承而已。而必須呼應二十年來的種種國際、兩岸及台灣內部變化,在總結和繼承之餘,帶來新的超越與改變。
這樣的改變,顯然還在醞釀當中。
這自然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而需要應試的,也遠非盧秀燕市長一人而已,而是整個世代。
更多 全球視野
【一份重構國民黨的新時代倡議:《藍晒圖》 新書發表會。】
【林家興:台灣國防關鍵在預算之外的「3大隱憂」。】
【顧長空:淺談在野黨在大罷免後的國際戰略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