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於 10月07日2025年
707
【藍晒圖:重構國民黨黨務改革&人才甄補搶先看。】
注目焦點
- 【藍晒圖|〈吳展良:「孫中山思想:內涵演變與歷史實踐〉搶先看。】11月12日2025年
- 【藍晒圖|〈張智瑋:「數位時代的巨浪,國民黨如何因應?」〉搶先看。】11月07日2025年
- 【藍晒圖|〈施威全:「民族統戰話語,國民黨如何接招?〉搶先看。】10月21日2025年
- 【藍晒圖:重構國民黨黨務改革&人才甄補搶先看。】10月07日2025年
- 【讀者投稿|胖橘約翰:綠媒為何不打鄭?國民黨的死亡預知紀事。】10月05日2025年
- 【藍晒圖|〈吳展良:「孫中山思想:內涵演變與歷史實踐〉搶先看。】
最多人瀏覽
關注我們
圖文藝廊
This error message is only visible to WordPress admins
訂閱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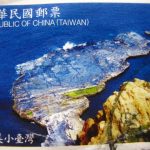













〈藍晒圖:重構國民黨黨務改革&人才甄補搶先看。〉
編按:本書出版時刻適逢國民黨主席選舉,在「誰當主席」之外更重要的事,可能是如何才能解決這些國民黨長年累積的深刻黨務問題,包括黨的制度改造、組織重組、人才培訓等,都比眼前的口水之爭更加值得我們關注,故首先放出第二篇章的導讀並略作調整文字,帶領公眾與讀者們了解本書著墨國民黨改革的重要一部分。
從在地經營到人才培育以及論述的欠缺,我們邀請到十二位黨內外的青年政治工作者、民代、黨幹部、媒體人、學者專家為我們一同剖析這些問題,並以實務經驗提出他們的解方,其中四位聚焦「政黨組織與人才甄補」問題,值得當前參選黨主席者深思。
⇲ 新書發表會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gkR2eKWBSyabufki9
⇲ 本書預購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pEoF7RZWgdyKcyp19
第二篇章:「黨務與在地」當中「政黨組織與人才甄補」小節節錄。
政黨的制度組織與人才甄補,也是國民黨自剖與重設計的關鍵標的。
國民黨組發會副主委陳克威,先針對國民黨的「剛性」體質,與「外造政黨」的屬性提出改革倡議。他指出,因應後工業化社會的高度分眾、議題流動,國民黨應朝「柔性政黨」調整,提升黨組織的適應性與包容力。其中包括對派系的接納與管理,以及給地方黨部更多自主空間。
該文更闡述,國民黨應採「決策機制內造化、社會溝通再外造化」的雙軌策略——他認同江主席任內,藉提升民選公職在中常會的比重,拉近黨意與民意的努力,但其同時主張,國民黨須同步強化與各種社會團體的聯繫,形成跨領域、多元的社會基盤。展望未來,該文更拋出國民黨應考慮推動「內閣制」憲改,並以此為中長期改革的參照。
“政黨要走向柔性化,需要橫向與縱向的觀念鬆綁。橫向,是接納「派系」的存在與共生,從對派系「避之唯恐不及」轉向「良善制度管理」;縱向,是鬆動中央集權,給基層更多空間。
很多人批評國民黨「派系分化」,但我認為派系本身不是壞事。其實「派系」 是在選舉壓力與競爭下,在政黨內部發展出來,以政治理念或政治利益結合的黨內組織形式。臺灣其他主要政黨亦存在派系,且能形成良性競爭。國民黨來臺初期, 曾為了團結度過難關,掃除中央派系,只容許地方派系的競爭發展。
過去派系會成為問題,關鍵在於欠缺配套的制度管理系統,以及政治人才甄補明確的渠道機制,才會變成黨內各自為政、爭權奪利,甚至內耗、內鬥的派系分贓結果。然而參考國外政黨的做法,例如英國工黨即有「黨內協調小組」、「派系登記制度」等機制,讓派系成為體制內刺激多元新創的的存在,追求有效管理,而非為了「團結」而動輒訴求廢除派系。
除了接納派系共生,黨中央也應給基層更多空間。”
新竹市黨部主委李縉穎則從地方黨部視角出發,分析國民黨的黨產查封、資源斷流對地方組織的衝擊,以及目前黨中央靠在地派系、民選公職「反哺」的權宜作法, 長期下來可能造成「地方割據」影響黨內人才甄補、輪調、新人培養的流弊。不過該文也把當前的資源短缺,視為政黨文化轉型的契機—例如從過去大撒幣的選舉動員,走向「兩瓶礦泉水」的節約戰法;黨員繳黨費也變得更彌足珍貴,更浮現過如「小額募款」或「黨籍訂閱制」等創新發想。該文還倡議,應發展理念導向的「參政聯盟」,並將地方黨部轉型為治理中介平台。
“理念驅動的「參政聯盟」
首先,是構築以理念驅動、跨域整合的「參政聯盟」,作為人才匯聚、橫向協作的新機制。當前國民黨中央集權式微,地方派系主導又有系統風險,此時亟需轉向一種更具彈性與多元性的組織形態,以適應分散化的政治環境,以及跨世代的合作需求。
所謂「參政聯盟」,指的是一種鬆而有序、以理念為核心的跨區域、跨領域人才群體。它不以既有地方派系為基礎,也非依附於特定領袖,而是透過議題導向與價值認同,所形成的多軸連結體。其不服務於一家一姓,而是與國民黨這個大家庭共存共榮、相輔相成。無論何人走上黨的權力高峰,都可幫忙執掌黨權者把國民黨作大作強;真正的人才,也不會因哪位主席或要角下台就被棄而不用。
此一聯盟的核心價值,在於促進黨內橫向整合與跨層級流動:橫向可打破既有地方派系對人才的壟斷,促進不同區域、不同背景從政者間的對話與資源互通;縱向則有助於打通中央與地方間的政治任用與政策落實機制,使地方不再是邊緣地帶, 而成為國政人才能夠下沉與磨練的實驗場域。
這樣的參政聯盟,不僅能協助國民黨重構內部人才養成制度,更能回應現今選戰操作的現實需求。以沒有派系奧援、挑戰艱困選區年輕候選人為例,常遭遇缺乏選戰資源、組織支援,與專業輔助團隊的困境。透過聯盟匯聚的人才網絡,不僅能媒合金主與候選人,成為政治資源交換的制度中介,也能提供政策設計、媒體操作、群眾動員等實務支援,成為一組共享的外掛「戰鬥小隊」。
此外,參政聯盟也能扮演政黨專業人才的輪轉平台。許多有治理潛力、具政策視野的年輕專業人才,若無適當機會歷練,難以轉型從政。反之,地方派系出身者雖擁有基層組織力與地方連結,但若缺乏專業輔導提升視野,難以跳脫地方侷限。透過「參政聯盟」內部的人才協作、輪調與支援制度,雙方皆能相互補位,進而孕育出兼具在地深耕力與治理能力的新型政治領袖。
這種制度性的整合,也有助於回應國民黨當前黨內「人走茶涼」、權力更迭後組織斷層的問題。以理念為基礎的人才群體,即使領導人更替,亦可保有基本的延續性與制度穩定性,使黨務運作不再過度依附於特定大老或山頭,而能逐步重建政黨的組織韌性與再生力。”
臺北市議員徐弘庭則聚焦國民黨的世代困境,並從政黨行銷、組織結構與人才甄補三方面討論。當代行銷戰場早因科技與社媒崛起而改變,但國民黨來不及轉型, 仍仰賴的傳統組織戰法,自難以吸引年輕人。組織型態上,徐將國、民兩黨比喻為「中小企業聯合會」與「控股公司」,對比黨內分工邏輯的差異;他也指出,藍營年輕人才苦無晉升管道,容易出走,綠營體系在人才甄補上則更有系統優勢。他認為, 當代政黨競爭是一場政黨「現代化」的比拼;國民黨須快速跟上。
“ 當代國民黨除了地方派系,黨內沒有明顯的派系競逐。每位民意代表與政治人物基本上就是個「中小企業主」。他們必須自力更生,負責議題研發(政策論述)、營運管理(選民服務)、品牌行銷(個人形象)以及財務行政管理。這樣的結構, 雖然賦予每位政治人物極大的自主性,但同時也意味著資源分散,缺乏中央協調與整合能力。
若以企業角度來分析,國民黨較像是個「中小企業聯誼會」,雖然每位經營者都有自己的生存邏輯與核心客群,但卻缺乏規模經濟與品牌協同效益。從個人能力來看,中小企業主的個人能力當然遠超一般業務員;但當需要面對全國性的市場競爭時,卻顯得乏力。特別是選舉如同消費行為,得東奔西跑親自談生意、維持公司運作的中小企業主,單論行銷能力與業務績效,可能難以追上只專注於行銷的業務員。
對比之下,民進黨的結構更像是一家「控股公司」。其黨內有清楚「派系」,各派系就像是企業集團內部的事業群或子公司,能夠提供統一的資源整合與策略支援。對於新進的政治人物而言,只要加入特定派系,便能依靠「中央廚房」提供的政策研究、資源分配與人脈網絡,讓他們專注於選舉與民意經營。甚至極端情況下,只需扮演「前線業務」的角色,其餘行政、策略與資源分配皆由派系處理。專業分工下, 能讓業務員完全專心在目標上,成為幾個系統對抗一群中小企業主的局面,展現競爭優勢。”
任職於公務機關的倬壬(筆名),則從太陽花運動激盪出的社會力開始,對照過去十年藍綠政黨「社會力介面」的變化,分析藍綠博弈。他指出,過去國民黨仰賴官僚資本與地方扈從體系,高度仰賴地方黨部、周邊組織,以及涵蓋農漁會、商會等建制型團體;相對而言,民進黨從社運起家,有更多元互通的智庫生態系,並對批判型、倡議型組織更熟悉。國民黨若要強化連結社會力,他提了三個方向:拔擢青年、廣納賢達,以及與公民團體就議題展開合作。
“社會力介面:藍綠生態對比
過去國民黨仰賴官僚資本及地方扈從體系,有效吸納來自地主、基層公務員、中小企業主的保守力量,形成綿密的人脈與利益網絡,維繫其政權基礎。自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開放民眾結社遊行、媒體出版、組黨參政的自由,釋放了更多元、批判的社會力,催生各色議題導向的公民團體。這些新湧現的社會力,則與同期發展的民進黨較親近。
國民黨傳統上與社會力的連結,高度仰賴正規的地方黨部系統—不管是黃復興黨部,還是各地婦工會、青工會、社會、青年部等,都是由黨部給經費,辦座談會、餐會來聯繫基層小組長及黨員,構建出的核心支持群體。這些人是藍營各類集會活動的基本班底、組織動員的網絡。
對照民進黨組織文化,民進黨也有自己的正規軍,例如黨內舉辦國務青營隊, 招募青年入黨。不過,民進黨各派系均有屬於自己的社團組織,例如小英基金會、新文化基金會、新社會智庫、辜寬敏基金會、臺灣教授協會、凱達格蘭基金會、青平台基金會、臺灣智庫及林義雄基金會等,均由不同派系資金來源所創立,打造出一種相對多元的生態系,而能更廣泛地接觸不同議題與人才。
民進黨的源頭,就來自一九八〇年代各種社運力量的集結,包含早年的農民運動、工人運動、環境運動、婦女運動等。多年以來,民進黨比國民黨更熟悉社運界的脈絡,也十分善於運用這些體系外的團體,不僅吸納相關議題納入政綱,也從群眾運動中尋覓栽培政治接班人—例如昔日的「野百合世代」,以及蔡政府重用的社運背景從政者。
不過當社運背景人士進入執政團隊,也必須面臨現實政治的取捨,不能再像過去充滿理想主義地衝撞。當他們也開始「顧全大局」,以政局穩定為優先時,也不免會與最初信念拉扯,甚至與早年社運同志出現嫌隙,替在野黨創造離間拔樁的機會。”
更多 公共時評
【藍晒圖|〈吳展良:「孫中山思想:內涵演變與歷史實踐〉搶先看。】
【藍晒圖|〈張智瑋:「數位時代的巨浪,國民黨如何因應?」〉搶先看。】
【藍晒圖|〈施威全:「民族統戰話語,國民黨如何接招?〉搶先看。】